


时间: 2024-11-17 22:55:39 | 作者: 塑料垫块模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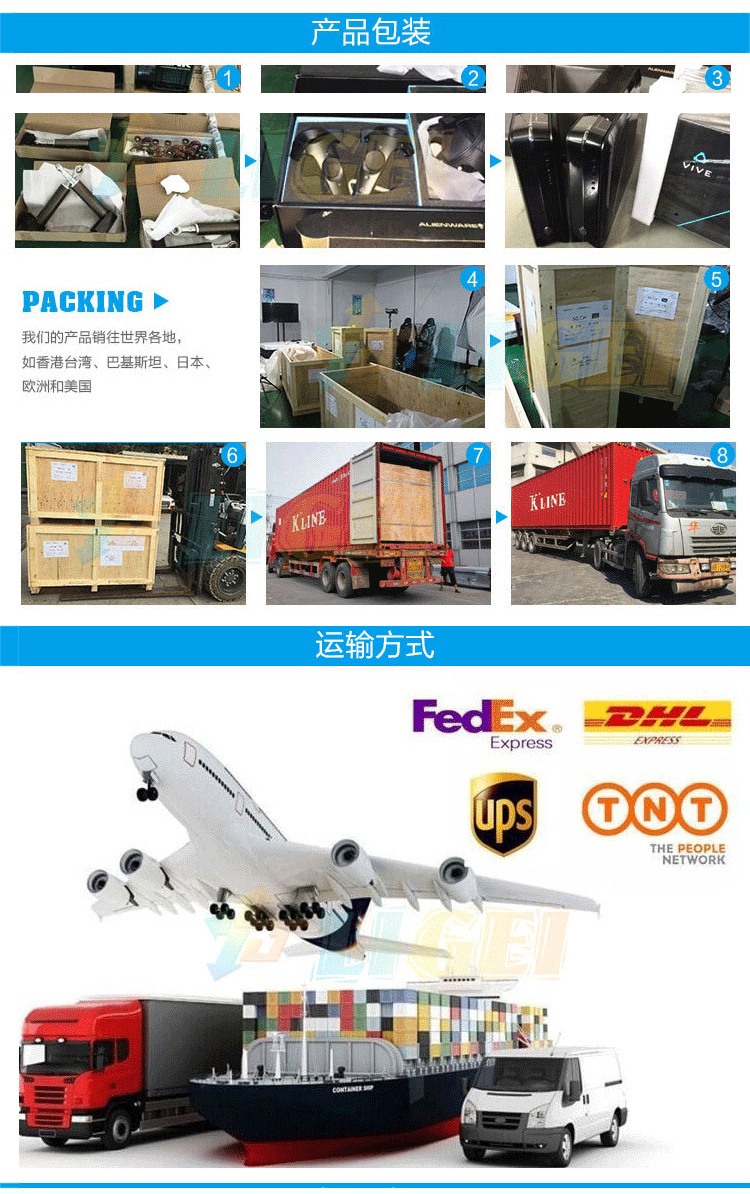
近日,华创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铭受邀参与36氪「CEO锦囊」商业航天专场节目的直播活动,他与天仪研究院创始人兼CEO杨峰、未来宇航创始人兼CEO牛旼就“卫星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这一话题展开了交流与探讨。
作为专注交叉科技前沿生产力的早期投资者,华创资本在2018年以早期投资人的身份领投了
蓝箭航天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商火箭企业之一,也是全国首家取得全部准入资质、唯一基于自研液体发动机实现成功入轨的民营运载火箭企业。
成功完成了朱雀三号可复用火箭十公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的任务,这也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为将来实现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发射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熊伟铭提到,从2018年投资蓝箭航天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年,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领域,“这也是VC行业的意义所在——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些前沿行业的早期发现和建设。”
此外,他在直播中从中美的历史阶段、地域、代表性企业出发,强调了合理竞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重要性。熊伟铭表示:“火箭、卫星,还有别的的一些辅助设施和服务,共同构成了商业航天生态多样性的关键。在今天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大家都应该放眼全球,不打价格战,而打差异化,假以时日一定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完整生态。”
熊伟铭:卫星在历史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假如没有苏联在1957 年 10 月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其实也就没有今天的硅谷,甚至今天的中美关系可能都是另外的剧本。
在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之后,美国人才想到自己的技术已落后,因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历了“艾森豪威尔假寐期”,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厉害了我的国”的状态中,直到苏联发射卫星,美国才开始建立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1958年《美国公共法案85-568》签署后,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硅谷开始做半导体。
如果没有苏联那颗卫星,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直播,更不会出现Google、YouTube这一些企业,正是这样的竞争,直接把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大国的科技,推到了最顶端的位置。
最顶尖科技的竞争,其实反映的是背后的经济实力。大国竞争是科技发展的加速器,包括当下热门的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某一些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国之间科技竞争的压力。
Q:中国民营航天这几年在加速发展,如果追赶SpaceX这样的企业还需要多久?
熊伟铭:咱们不可以简单站在当下这一段时间点去对比美国的同时期,还是要放大到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不仅仅是商业航天领域,从创投行业出发去思考,也能看到背后结构化的差异。
在单位经济指标方面,美国的人均 GDP 接近 10 万美金,我们大概是一万多美金。而全球所有的长期资金市场加在一起大概 109 万亿美元,美国大概是 50~60 万亿美元,中国大概是11~12 万亿美元,美国一家就吃掉了全球一半的长期资金市场的份额。
当年我经常和美国的投资人讲:美国有雅虎,中国有新浪、搜狐、网易;美国有eBay,我们有易趣、淘宝等。现在你们有SpaceX,我们也有蓝箭航天等企业。所以我们今天长期资金市场的行业结构其实和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非常类似,但购买力不一样。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的话,我们可能会再拖后十年,也就是上世纪 90 年代左右,所以从时间点上,我们要比美国同行落后 25 年左右。我们的容错机制美国人也都经历过,SBIC(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 最早也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借款的方式扶植美国的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因为要和前苏联对抗,所以美国要扶持科技力量,国家批钱我再借给你,但结果发现这样的形式并不好。
我们才刚刚走到这一步,从制度建设、演进的节奏上来看,有点像小时候我参加高考,我问过好多师兄师姐,高考需要注意什么?但如果你没有真正参加过,你就不知道高考是什么。参加过之后,噢,原来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制度建设就是这么个事儿。和高考一样,只不过它有无数次的小考。你不经历过,别人再怎么说那都是别人的经验,你必须要自己走到今天才可以。
商业航天现在得到了巨大的支持,目前是非常好的发展期,但可能我们该对应的不是 2024 年的SpaceX和它现在的生态,而是2010年或者再晚一些。
Q:对于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投资人,有哪些影响行业发展的因素至关重要?
熊伟铭:我还记得当年去蓝箭航天做尽调,那时候我正迷恋 SpaceX,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像SpaceX 那样年轻的专家,比如 Tom Mueller?(SpaceX 前退休CTO)然后蓝箭的兄弟指着某个同事说,那个人就比 Tom 强。当然我们得承认,SpaceX确实是先行者,积累了很多 Know-how,所以它走过的弯路我们也得走一遍,也得参加高考、小考、模拟......各种各样的考验。
就在前几天的9月11日,蓝箭航天朱雀三号VTVL-1试验箭成功完成十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飞行试验任务,所以这些事情都得一步步做。我们从2018年投资到今天,这个行业发展已经很快了,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实业,因为真的很难很难很难,更关键的是需要更多发星的客户,这样钱才能转起来。
同时,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宽容一点,允许失败。若无法失败,马斯克早就不行了,美国就没有硅谷,变成“死亡谷”了。
如果大家不想死,就不创新、不发展,只是苟着,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应该冒险干这个。
我觉得还要整个社会从文化上、气氛上,最后可能体现到规则制定上,是不是能有更宽容、更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文化?
其实越大的公司越需要竞争对象,这就和生活中的平衡一样,你忽然变成了全年级第一,那可能 985 都考不上了,因为你是最好的了,就不了解什么是更好的,所以我觉得竞争是随随处处需要,但不是过度竞争。
这一点上为什么硅谷做得比我们好?因为他们的长期资金市场实现了资源调配的功能,别人做这个值 100 块,我只值 5 块。那嘛还做这个呢?错位竞争对所有人都是值钱的好事情,但头碰头的竞争下其实第二名会很不值钱。这一点上,美国的长期资金市场也比我们敏感,他们在资产定价上非常高效。我们的长期资金市场是比较弱小,经常无法出清。
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另外一面, 就像 Beatles+斯普特尼克——一边是文化,一边是科技。假如没有资产定价功能,科技行业不会特别健康,会浪费大量的资金在一些重复建设上。
我们今天对标的仍然是美国的七八十年代,美国1972年创立了 Sequoia Capital 和 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1977年创立了 Matrix Partners,所以美国是上世纪70 年代中后期慢慢的出现VC,干了十来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有VC。我们要承认发展水平、阶段的不一样。纳斯达克刚出现时是非常不入流的,为什么现在变成最主流的市场之一?因为它是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仍旧是呼唤市场机制下的自由竞争。
市场机制很重要,美国其实也有计划经济,假如没有 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的科技不会这么发达。先有计划,再用市场引导,才形成了今天的百花齐放。
没有竞争的环境出不来强者,为什么 SpaceX 做得比所有国家的航天都要好,因为航天过去都不是产业。我记得最早蓝箭尽调时我们比较关心供应链如何来解决?如果都是“高师傅李师傅敲出来的”,那成本肯定高。任何一个时间里如果能商业化,就能迅速把供应链的成本拉下来,然后就能出现个人化的卫星。像当年的计算机,如果按 50 年代 IBM 的说法,全世界有三台就够了。所以这么多东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产业的迭代肯定能实现,只是得允许中间出现这么多的玩家,资本得循环起来。
Q:马斯克其实是作为“外行”造就了SpaceX这个超级力量,这给创业者、投资人是否带来过一些启发?
熊伟铭:如果看最近 30 年的科技发展史,全是外行人用科技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点,所以找到应用的PMF 特别重要。
我一直记得当年千团大战见王兴时,大家认为他是网络人出身,没有做过线下,似乎缺乏餐饮行业的禀赋,就质疑他能不能行。但为什么最后美团能跑出来?我觉得是因为他懂用户,创始人只有了解用户,才知道技术要如何为用户服务。说实话,原来我是倾向技术至上的,总是希望技术特别厉害,是那种别人都做不出来的,所以遗憾错过了。
现在创投市场上有两种类型的项目,一种是命题作文,市场已在那,可能就纯拼技术了;另外一种是我有一个超级技术,但怎么找到市场?比如
卫星、火箭这类项目的创业,对用户的了解就很重要。我觉得这么多场仗下来,只有了解用户、了解场景,这样的团队很可能才是最后的获胜者,但早期的时候他可能没冠军相。
对于创业者来讲,创业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是一个慢慢的提升、不断演进的过程。个人的成长能力、学习能力其实非常重要。
当年的苹果、特斯拉、英伟达的创始团队,都是一帮不靠谱的年轻人,都是“Under dog”,但最后成就了今天的科技。所以我觉得判断人和项目时还是不能有成见。
Q:目前卫星公司可能还是 to 政府的客户会比较多。畅想一下,未来还有哪些商业场景可以期待呢?
熊伟铭:物业规模比较大的商业机构未来应该有这个需求,比如太古里等地产公司目前可能暂不需要特定的服务(如卫星监测),但可能20~30年后会需要。要满足这样的监测需求,就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这不仅仅是遥感技术的应用场景,更是卫星技术潜力的巨大体现。
未来,我们是不是能找到创新突破点就变得更外重要,一旦这个点实现正向且持续的现金流,就将对整个行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例如,在互联网时代,最早 Palantir 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神奇,为什么有这么一家私人公司能和美国政府合作?我觉得这么多东西都是有非常强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市场行为。不止是遥感,可能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应用场景。
Q:大模型在遥感领域一直在使用,随着大模型能力的增强,以及遥感数据的丰富,大模型能发挥的作用还有哪些?
熊伟铭:目前在这样的领域还没看到那么多不同的应用,我觉得现在有点像上世纪 70 年代的PC,当年的Apple-1能干的事情非常有限,都是一帮极客在用。就像2012年的大疆无人机,除了航拍,也不知道还能用来干什么,但是现在,美团在深圳的自动送货无人机,已完成了几十万次的飞行。所以,这些技术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先建立能力,有了网络之后,各种奇思妙想的应用才会出现。
也许不是我们这代人来实现,而是 00 后或者 10 后,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大堆的卫星可以用,比如星链、GW,还有各种气象卫星,甚至有可能还有中继服务。他们可能会想出我们很难来想象的应用。比如,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更准确的天气预报,或者我是个农场主,我想知道土地的详细情况,包括土壤成分,或者极端天气的可能性。我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年365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如果这样的订阅用户多了,就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但从现在这一段时间点来讲,我觉得我们仍旧是争取全行业能多发一些卫星,把网络连起来。这颗星不在的时候,其他的卫星能不能像手机漫游一样接管服务?早年手机漫游还要收费,现在卫星的情况也类似,因为我们的卫星还不够,基站也不够。
现阶段首先要提供足够的供给,每个行业出来都是先有供给,应用才会发展出来。
我还想到两个科技领域的商机:一个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强大的、低功耗的推理芯片。如果我们有这种芯片,就可以让卫星在天上直接处理数据,而不是把原始数据传回地面。900兆/秒的传输速度太慢了,不如让卫星直接返回处理结果,这样更高效。比如我们大家可以在卫星上进行数据处理,然后压缩数据,再用推理芯片来达成目标。看看黄教主(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或者我们的上市公司能不能开发出这样的芯片。
另外一个生意是我每天、每小时或每分钟积累这么多的数据,到最后那个数据往下传,还不如有一个可回收的存储设备,就像AWS Snowball 一样,它其实就是一辆卡车,用来处理大量数据。如果数据太多,就不用传了,我可以直接开车过去把数据给你。比如,定期一个月或一年,给你送回一次数据,给你一个盒子,一个存储设备,然后你自己在地面上做多元化的分析和训练。这样可能更划算,而这些都与AI的计算能力和算力息息相关。
发卫星还是要有场景,为什么发?谁出这个钱?当时我们投蓝箭时,他们最开始要做一个固体火箭发射,然后我们就讨论有这个必要吗?因为最后你是要做液体火箭,为何需要先发个固体?后来我们理解了,因为只有发射动作才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所有的证照、评分......我们这个运营团队才能得到锻炼。
所以,一旦进入长期的发射或者是要干这些事,还得想明白我们那个市场在哪?谁在花钱干这个事情?因为股东、投资人的钱也是很有限的,还是要从市场找机会、找钱。
Q:9月11日蓝箭航天可复用火箭 10 公里级垂直发射也试验成功了,这对我们国内低轨卫星组网有哪些比较积极的推动作用?
熊伟铭:今天卫星的成本已经降了两个数量级,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这个时代下,全球都在关注商业航天的产业机会。
我们的目标就是更便宜,就像 GPU 打比赛一样,如果你说要对标 A100 ,那你已经落后了,你必须看H100。追上星链,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但赶上猎鹰 9 号指日可待。
如果按照时间表来看蓝箭这次 10 公里的实验,理论上明年,也就是可能再给它 12 个月,就能够直接进行商业化的发射;商业化发射规模再往后一年,到了2026 年,成本就开始往下掉,可能每公斤的成本就能接近3000美金左右、大概人民币2万多元,这是我拍脑子算的。但2018 年我们开始干的时候这一个市场可是20万,就六七年时间,成本直接降到少了个零,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带来了行业的一个共识——降低成本。
可回收实际上也是为了降成本,就能重复使用这一些东西。成本下来之后,还需要更加多的SAR卫星、通讯卫星准备好,能找到自己的使用场景。在一个高利润的行业里面,最重要的是稳定可靠,说何时发就能何时发。我的猜想是三年以后所有公司的价格都会达到那个水平,那火箭公司就需要差异化竞争,也许是客户上差异化,也许领域上差异化——就像物流公司,最早有宅急送,后来有“四大家族”,而 EMS 也有它的生意。
包括出海,在这里面国际化或商业化的哪种形式,能够在今天这么复杂的地理政治学环境下可以维持住?可能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策略。
中国的火箭公司、卫星公司,肯定是全球性的。虽然这个技术要待在国内,但客户、服务,要看全球性的需求。其实海外很多场景都是非常成熟的,国内可能还没形成,我们尽量不打价格战,而是打差异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利好,再给三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的卫星就会集体像下饺子一样上天。
一旦那个市场起来之后,很多需求就找到你了。打个比方,早年我们全公司用一个 Email 邮箱,还要每个月收 30 块,所以 Email 是个杀手级应用。我相信卫星也会逐渐出现一些 to C的杀手级应用。但在那之前,市场的需求也足够这些卫星公司、火箭公司饱餐一顿。当年的IT 行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涌现了大量的 PC 厂商,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比如康柏、DEC 、AST这些消失了的主机厂。
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是这样,电动车、手机是这样,火箭、卫星以后可能也会这样,慢慢集合成几家头部公司,或者再加上一些垂直领域里面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然后再以中国的姿态去参与全世界的竞争。